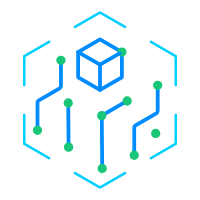学术观点 董洁:从“农民工”到工人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
学术观点 董洁:从“农民工”到工人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
学术观点 董洁:从“农民工”到工人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入口广场景观,泉州景观设计,浦东景观河清华大学外文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语言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身份认同研究、移民研究、语言与全球化、语言与新媒体、语言政策与规划。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虽然他们多从事与工业和服务业相 关的工作,但户籍上登记的身份仍是“农民”, 因此传统上常被称为“农民工”。然而,许多人并不认可这一身 份称谓,认为它反映出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艰难处境。对北京东部一个流动人口社区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发 现,城乡劳动力人群在努力摆脱“农民工”这一称谓,他们的子女对城市具有较高的认同,但是他们常常被社会 以多种方式进行区隔。对其语言使用和身份认同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探讨城乡劳动力人口的“工人”身份构 建,可以看出深度城市化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流动人口返乡进行新农村建设是城乡发展的一个方 面,但是对于大部分选择留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劳动力人口的市民化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人身份构建成为城市 发展的重要命题。从“农民工”到工人,城乡流动人口自身和整个社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献来源:董洁.从“农民工”到工人——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J].语言战略研究,2021,6(3):25-3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深,城市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进城务工人员达到 2.9亿,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当前的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数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具有在城市中生活时间较长、在城市建立家庭并养 育子女等特点,早已不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人口农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回乡耕种的“农民工” 了。而且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城市中出生并成长的“打工二代”,对于城市生活比乡村生活更为熟悉。然而,由于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仍然是“农民”,因此传统上常被称为“农民工”或 “民工”。虽然这一称谓有其实用性,而且已经在生产生活、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等领域广泛使用,但是许多人并不认同“农民工”这一身份标签,认为这个标签隐含了“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的过渡 性身份(De Fina et al. 2006 ;Dong 2020)。
“农民工”这一称谓反映出许多城市在接纳城乡劳动力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 城市的发 展离不开大量劳动力。中国过去 40 余年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源源不断、训练有素的城乡劳动力人口。另一方面,城市的快速膨胀引发人们对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系统的担忧,比如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紧缺,户籍儿童跨区、跨片入学难等,因此人们对于非户籍儿童在城市就学有较大顾虑。再如几年前空气污染、雾霾严重,部分原因是城市机动车流量大、二氧化碳排放量高,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城市承载能力的关注。然而,城乡流动儿童需要满足的是其义务教育需求,因此极少 “占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Dong & Blommaert 2009)。同时,城乡流动人口私人小轿车的拥有比例较低,他们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电动车或自行车,因此产生的机动车尾气有限。可见,许多关于 城乡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并不准确。
国外许多大都市在发展进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以伦敦为例,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全球首个实现城市化(城镇人口)比重超过 50% 的国家。伦敦人口 1800 年为 86 万,1850 年 增长到 232 万,至 1900 年则增长到 658 万(陈胜昌,等 2005)。二战以后,英国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 战后重建工作。由于战争造成的人口短缺,大批劳动力移民涌入英国主要城市。他们活跃在采矿、建 筑以及服务行业。在伦敦,多数移民在伦敦东部的码头区和港口从事体力劳动。起初,许多英国民 众的心理预期是,这些劳动力移民只是短暂停留的临时打工者,工作结束后他们就会返回其母国。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人留了下来,从事体力劳动、建立家庭、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孩子也多以英语 为母语,并形成相应的身份认同。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也都类似,发展速度快,人口增长幅度大,移民不断本地化和市民化,这里不再赘述。
伦敦的具体情况虽然与中国大城市有诸多不同,但无论是中国自身经验,还是国外相关案例,都显示劳动力人口市民化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城乡劳动力的市民化身份构建也成为一个重要 的命题。近年来在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领域,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教育水平、能力素质、社会融入,以及他们在住房、就业、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王晓华 2019 ;蔡鹏,严荣2020 ;蒋飞云 2019)。这些研究致力于解决城乡劳动力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对于他们的社会定位、身份认同和长期发展等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仍然比较缺乏。虽然不少研 究以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为方向,但多着眼于阐述他们应该如何融入城市生活这一问题。在国际移民研究中,“融入”主要指移民放弃自己原有文化, 完全吸收移入国文化(Berry 2005)。由于这种 主张“被吸收、被同化”的观点以文化不平等为基础,既对移民不公平,又难以实现,因此已经被国 际学术界摒弃了。虽然我国城乡移民与国际移民有一定区别, 但是就其社会融合来说则具有共性。城 乡劳动力在市民化(包括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人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过程中,在成长经历、生活习惯、语言特征、文化习俗等方面呈现高度的多样性,不应该用一些研究中所谓的“文明素质水平 相对较低”“与城市现代文明的要求有较大差距”等对他们进行污名化和边缘化。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城乡劳动力人口研究主要聚焦于普通话和方言的语言态度、语言选择、普通话交际水平、家庭语言政策等问题(如刘玉屏 2010 ;石凤 2018 ;夏历 2007,2017)。近年来,打工者及其子女的语言身份认同研究也日臻成熟,从言语交际和元语用等层面探讨这一群体通过不同语 码之间的选择和转换、对细微语言特征的使用以及对自己和他人语言特征的评价,构建身份认同(如 董洁 2011,2014,2016 ;Dong 2009,2011,2013,2017,2020 ;付义荣 2016)。通过语言的使用而构 建的身份被称为语言身份认同。人们在不同的语言使用层面上构建身份认同。在交际互动层面,人们通过多种口音之间的转换来构建身份,他们的某些语言特征也会“透露”他们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身份认同要素。在元语用层面,人们可以通过对语言使用特征的评价话语进行身份构建,比如表达某种口音“好听”“绅士”“土”“可笑”等元语用评价可以反映出人们对该口音是否认同(Dong 2011 :45 ~ 51)。以英语为例,许多英语学习者认为标准英语“好听”,显得有教养、有绅士风度,因此也倾向于学习和模仿这种口音,从而构建“高学历”“国际范”等身份认同。在某些语境中,中 - 英语码转换还可以构建大都市的“雅皮士”身份 (Zhang 2005)。因此语言的使用在身份构建过程 中占有重要地位。
研究对象如何评价自身的语言身份,尤其是如何称呼自身及其所属的社会群体,是语言身份认同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限,因此本文通过流动人口对自身群体的 称谓,如“农民工”“打工人”“流动人口”“新工人”,探讨他们在元语用层面构建的语言身份认同。本文报告北京市朝阳区一个流动人口社区的民族志语言景观语料,并分析其中 3 个案例语料。与传统的语言景观研究不同,民族志语言景观研究不仅讨论公共空间展示的语言文字,而且通过长期在该空间生活和观察(参与式观察),以及与其他空间使用者,尤其是语料的生产者和使用者讨论(深度访 谈),给他们以发出“声音”的机会,力图多层次、多维度、准确地解读语言景观语料。本研究从笔者 2017 ~ 2019 年收集的 115 份景观语料、42 份田野日志中,选取 3 个最具普遍性并且反复出现的流动人口对自身称谓的语料个案进行报告和分析。
本研究的民族志田野是北京东部的一个城中村。那里的村民曾经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是由于近年 来北京城区不断扩大,与其他许多城中村一样,这里也逐渐成为城区的一部分。虽然附近区域已经是高楼林立,但是由于这里紧邻首都机场,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不适宜商业开发,因此仍然保持着城中村的典型样貌(Sun 2014)。许多村民已经迁出,留下的村民翻盖了房子,租给来北 京打工的城乡劳动力。这里房价便宜、交通方便,备受打工者青睐。多年前,一个打工者社区搬到这里,自发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图书馆、博物馆、小型剧院、二手商店等,为城乡流动人口服务。他们还定期举办艺术节、演唱会、打工春晚、专辑发行等文化活动,丰富城乡流动人口的业余文化生 活,并将收入(如发行专辑的收入)用于建立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为居住在周边地区的流动儿童提供 受教育的机会。这个劳动者社区受到了媒体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本文 3 个 案例包括该社区的语言景观研究(案例一)、“流动”儿童访谈(案例二)和该社区的主要创办人之一的访谈(案例三),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呈现和分析该打工社区及其居民的语言身份构建状况。
本文呈现的第一个案例是以语言景观研究方法在城中村采集到的景观语料(图 1、2、3、4、5)。这些景观语料都与城乡流动人口对自身的称谓有关,如图 1 和图 2 中的“打工”,图 3 中的“流动儿 童”,以及图 4 和图 5 中的“新工人”。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图 1)、打工文化艺术节、打工青年艺术团和打工春晚(图 2)等,是一系 列以“打工”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形式。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 2007 年由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起的 一家民间公益性博物馆,在创立过程中得到慈善公益捐助。这里的展品包括政策文件、照片、信件、工作证、暂住证、工资欠条、劳动工具、劳动制服,以及打工诗歌等文艺作品。博物馆的目标是记录打工生活,构建打工者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图 2 呈现的是打工艺术博物馆中的一个展板。打工春晚是由打工者社区的工友和义工们 2012 年开始举办的小型春节晚会,每年春节前夕专门为打工者举办,目的是使留守北京的打工者们也能度过 一个美好的除夕。与央视春晚不同,打工春晚并不邀请娱乐明星,也没有华美的服饰,而是用劳动者 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展现自己的风采,发出自己的声音(宋晖 2013)。
从这两份语料和该社区的文化活动命名来看,“打工(者)”是被这一群体认可的称谓。本文也采 用“打工者”来指代这一群体。“打工(仔)”一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香港传入内地,指工薪阶层或受雇者。随着影视作品如电影《特区打工妹》等的传播,“打工者”一度指从农村到城市外出打工的人。不过随着近年来“高级打工”“打工皇帝”等称谓的出现,在一些市民看来,“打工”似乎和城市 “白领”的含义更为接近。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打工人”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语,虽然被城市工薪阶层热捧从而带来许多社会关注,但其本来意义也在流行过程中被消解,其原本所指的人群在这一网络 狂欢中失声。
图 3 也是打工博物馆中的一个展板, 记录的是城乡劳动力移民子女在城市中接受义务教育的困境。“流 动儿童”(以及“流动人口”)在主流媒体和知识界广泛使用,但是这些儿童除了在中学阶段需要回原 籍参加升学考试以外,其流动性并不很强。许多“流动儿童”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来到他们 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有的则是在城市中出生和长大的。之所以称他们为“流动儿童”,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户籍不在城市。虽然近年来许多城市都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公立义务教育,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仍然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升入中学(Dong 2011)。“流动”一词含有“不稳定”“不确定”的意义,也 反映出他们不完全被城市主流人群(或重要他人)所接受的现实情况。但是以“流动”为名将他们与城市儿童进行区隔,必将对他们的长期社会化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影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追踪调查。
图 4 是该打工者社区内的小型剧场“新工人剧场”,图 5 是社区内部刊物《新工人》季刊(2010 年 1 月)的封面。这份内部刊物的内容主要包括多人撰写的对第二届新工人艺术节的观后感,社区成员创作的诗歌、相声等文艺作品,以及社区成员们对“新工人未来发展”“新工人文化”等问题的反思。知识界也使用了“新工人”这一称谓, 例如吕途(2013,2014,2017)的《中国新工人》三部曲,黄典林(2013)《从“盲流”到“新工人阶级”》和汪晖(2014)的《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中都用到了 “新工人”这一称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尝试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保障他们的权益,并建议将“农民工”更名为“新工人”。在大众传媒领域,主流媒体如《民族日报》于 2020 年刊登报道《“新工人” 成长记:从贫困农妇到生产组长》,《楚天都市报》也发文提议《一线农民工成长为新型产业工人》。可以说“新工人”是打工人群自身、知识界和媒体等不同群体接受度都比较高的一个称谓。
不过,“新工人”这一称谓在何时、被何人提出,如何定义“新工人”,他们“新”在哪里,与(老)工人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甚至“新工人”是否存在等问题都存在广泛争议(如袁长庚 2015)。打工群体内部也有类似的质疑声音,比如有工友指出“给农民工改名是画蛇添足”,因为他们 d 不在乎别人怎样称呼他们,而是在乎能否按时拿到工钱,自己的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也有工友,如本文案例三中的李先生,对新工人的“新”字提出不同看法。
为了从多个角度对这一人群的语言和身份认同进行研究,本文接下来进一步讨论访谈语料,包括 对一名在该城中村内生活和就学的儿童访谈和对打工社区创始人之一李先生的访谈。
在探讨城乡劳动力人群的身份构建时,其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重要的研究视角。案例二中的菲菲是一位 12 岁女孩,在社区组建的打工子女学校读六年级。在一次周六的课外活动中,笔者作为志愿者老师和菲菲分到一组做活动。六年级的孩子面对的主要难题是选择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升学。说是“选择”,其实他们没太多选择余地。由于对考生户籍和学籍的要求,打工子女留在城市并升入有竞争力的中学希望非常渺茫。在学业上继续追求深造的孩子需要尽早回老家读初中,以免耽误学业。午休时我们聊起老家的事,菲菲说“别人对老家留下的都是美好印象,我对老家留下的全是恐惧”(第 9 话轮)。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持类似看法的学生并不少见。多数孩子在说起回老家的经历时都会提到不熟悉当地环境和生活习惯的问题,有的表示他们不会说或者说不好家乡话。虽然他们对老家抱有好奇心和 亲近感,但是大多数表示不愿意在老家长期生活,究其原因,有的是和菲菲一样,觉得老家的生活难 以适应;有的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需要留在城市里继续打工,他们如果回老家就会成为“留守儿童”。有时候这些儿童也会受到一些苛责,比如被说成“忘本”。但是考虑到他们大多数是在城市中长大的,老家对他们来说主要存在于父母长辈的交谈中, 以及春节回老家过年的短暂经历中。因此他们对家乡的陌生感和城市儿童是类似的。同时,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城市语言(通常是普通话以及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的认同也显而易见。身份认同研究通常按照父母的社会阶层定义其子女的阶层身份,并认为子女的身份认同反映其父 母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但是案例二显示,菲菲及其他“打工二代”的身份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复杂。如果说他们的父辈能够接受丧失劳动能力后回到农村生活,打工子女们面临的选择和承担的压力则更加呈现多维度、多层面和不断变化的态势。正如前文所述,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不单单是自己决定的,也需要他人的认可(Blommaert 2005 ;Dong 2011)。对于打工子女来说,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有时候不能得到同伴、家人、老师以及社会中重要他人的认可,因此难以确立。同时,他们在老家的亲戚朋友会把他们当城里人看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是市民还是农民 比较迷茫,从而形成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身份认同。
案例三呈现的对话是李先生对周围人, 尤其是他的熟人和朋友使用“农民工”一词的看法。李先生 18 岁来到北京打工,2002 年和工友们一起创办了打工青年艺术团, 利用业余时间为工友们表演自编自演 的文艺作品。作为城乡流动人口中的一员,并且长期生活在他们中间,受访人(下文称为“李先生”)的看法在这一群体中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同时,由于长期服务于这一群体,李先生的观点对这一群体有一定的引领作用。笔者到访的时候,李先生正在电脑上和朋友在线讨论问题,笔者在旁边等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笔 者观察到他们讨论得很激烈,李先生有些情绪激动,因此在他们讨论结束后笔者询问了讨论情况。来他们在争论“农民工”这一称谓是否合适。在随后的交谈中,李先生把这些人分为 3 类。第一类是 “年纪大的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并且习惯了使用“农民工”一词,因此劝说他们 不再使用这个词非常困难。第二类人是“不太熟”的人,李先生和他们交流机会少,“一年也见不到两面”,因此劝说他们是“没有必要”的。第三类人是李先生的朋友或者熟人。当李先生明确告知他们不应该使用这个称谓,他们仍然继续使用,这令李先生不满。
李先生比较倾向于哪个称谓呢?笔者猜测“打工者”和“新工人”应该是可能的选项(线) 。对于李先生来说,“打工者”“新工人”都是可以的,但是“工人”才是最合适的称谓。为什么 “工人”比“新工人”更贴切呢?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用李先生自己的话来解释,“工人嘛,我感觉,就是工人”(线)和“其实真正的身份,就是工人”(线)。可以看出,李先生认为他们做的是工人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工人,所以没有必要从工人群体中把他们区分出来。
李先生对于工人身份的认同,与案例二中菲菲的城市身份认同有相似之处,都是既需要自我认同、又需要他人认可才能建立起来的身份。不过和菲菲不同的是,李先生构建的不是个体身份,而是群体身份(Agha 2003),但是这个群体身份没有得到群体的广泛认同,“有的工人就认为自己是(农 民工)”(线)。这种社会结构层面的定式思维被人们不断重复,并被自身所内化,传递 给他们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使之更加固化和难以改变(Bourdieu 1987)。对于这种情况,李 先生认为“他还是需要启蒙的,他没有群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这也就是他和同伴们创办打工社区的原因之一。
从宏观视角来看,农村“荒漠化”、新农村建设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劳动力回流现象逐渐显现;城镇的多元化发展,如卫星城模式,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然而对于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城乡劳 动力来说,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如何构建身份认同,如何长期发展,以及如何有尊严地生活,是每个 人乃至整个社会都要面对的时代命题。同时,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是其文明发展和社会公正 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文通过对民族志语言景观语料以及访谈语料的分析,探讨城乡劳动力人口及其子女的语言身 份认同。从“打工者”到“流动”人口和“流动”儿童,再到“新工人”,该城中村的多处景观语料 反映出他们为摆脱“农民工”这一边缘化称谓所做的努力,以及不断探索和构建其群体身份认同的尝试。城中村中儿童的访谈显示,许多打工子女在城市中长大,对城市的认同相对较高。虽然也有 例外,但是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持有这一看法的儿童和青少年比较普遍。与他们的父辈“落叶归根” 的观念相反,“打工二代”通常不认为自己迟早要回归农村。不过,由于升学的要求,他们却是面临 “回老家”最为迫切的一个群体。这与笔者在其他田野调查(如 2005 ~ 2007 年在北京宣武区某公立小 学的田野调查和 2009 ~ 2011 年在石景山区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相呼应(Dong 2009,2011)。
对李先生的访谈则把这一群体身份认同推向一个新高度。从田野调查前期的语言景观研究来看,“新工人”也许是这一群体接受度最高的称谓。不过李先生的回答表明,“新工人”中的“新”是没有 必要的,因为他们做的是和工人一样的工作,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工人,为什么要以“新”来进行区分 呢?如果他们是“新工人”,谁才是(真正的)工人呢?从“农民工”到“工人”看似是几个字的区别,实则反映出他们常年服务的城市对他们的贡献和身份的认可。然而这一称谓能否确立还需要满足几个重要的条件。首先需要得到群体内部的广泛认同。正如李先生所说,当许多城乡劳动力人口使用“农民工”指代自身、并且不对这一称谓背后的污名化含义进行反思时,他们的“工人”群体 身份是难以形成的。其次,当广大市民对“农民工”称谓习以为常和熟视无睹时,仍然认为他们在失去劳动能力时应该回归农村,城乡劳动力人口在城市中就难以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更重要的是,当大众传媒和知识界权威话语持续使用“农民工”指代这一群体时,人们的观念不断被固化,改变 就愈发困难。因此,笔者认同李先生的工人身份,认为他们从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工作,和工人没有区别。但不论是普通市民、媒体学界还是一些城乡劳动力自身,都需要对他们的劳动付出和社会身份进行更加 深入的思考和认识。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养育子女,做着与城市工人一样的工作,理应和其他市民 享有同等机会和权益,获得同样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被社会以多种方式区隔,他们的付出常常不被“看见”,他们的声音难以被“听到”。从“农民工”到工人,城乡劳动力自身和整个社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关文章
- 西安这个大手笔规划:303公里西安将诞生一条超级绿道!
- 客家地名文化景观聚类分析 ——以宁化县为例(下)
- 园林绿化养护师证书怎么报考?报考流程、报考条件具体分析!
- 适合摆放庭院公园的景观石—福州泰山石
- 创新产业园|工业园-产业园-产业社区的进化论
- 9月7日大连圣亚(600593)龙虎榜数据
- 榆林防腐木园林景观加工厂诚信厂家承接工地
- 盐池大水坑镇: 攻坚环境整治让旧貌换新颜
- 浙派园林造园者说|黄浩丞:杭州可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设计总监
- 长安欧尚X5带你到黄家花园三植物配置与生态景观
- 森林景观中渗透中国传统智慧 城市绿心24处林窗展24节气文化
- 一问到底丨国庆花卉景观是如何打造的?
- 成都规划水网体系彰显水景魅力
- 落定人居森林 铂玥江南超1000㎡景观会所助力圈层社交
- 玻璃钢仿真白鹭仙鹤雕塑 动物 景观
- 跨界融合对城市景观照明表现形式的影响
- 【聚焦】医疗卫生机构职工健康办公室样板间——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心内科
- 这几种小巧的树都可以作为室内的盆栽景观你更喜欢哪一种?
- 景观膜结构丨西班牙SPHERIFICATIONS装置
- 超美!惠东这个网红景点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