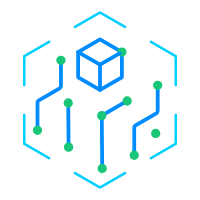雅昌×北京大学CMAA|香港当代艺术观察:从个体经验出发回望50年生态变迁
雅昌×北京大学CMAA|香港当代艺术观察:从个体经验出发回望50年生态变迁
雅昌×北京大学CMAA|香港当代艺术观察:从个体经验出发回望50年生态变迁,海水景观,微景观雾化器,耐候钢板景观香港的当代艺术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特别重要的方面,因为香港不仅是中国“一国两制”文化实验的前端,而且也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体制之下,世界和中国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实验基地。香港因地制宜的艺术政策和行政系统,涉及艺术的创作与生产,尤其是艺术的交流和市场等情况。香港不仅对中国是特殊的,对全世界来说也是特殊范例。所以,香港出现的当代艺术问题也许不仅是一个地方问题,还是一个全世界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
香港最近的发展,尤其是M+的出现,反映出香港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和运作的特点,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希望香港能够成为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了解整个世界当代艺术的津梁,作为在中国内地展现、推广和研究世界当代艺术的过渡方式,同时也成为世界对中国、中国对世界的当代艺术相互反应的试验基地。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新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香港当代艺术抱以了极大的关注和期待。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取得巨大变化和初步成就期间,我们就对包括香港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当代艺术的发展及其对改革开放的继续实验,尤其是实验艺术和艺术实验,抱以了很大的希望,对其艺术研究,对香港当代艺术创造在人类共同的精神上能否起先锋作用和引领作用,就一直有所期待。香港作为“世界设计之都”早就在世界声名显赫,但是在当代艺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经历了20年的发展,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总结和回顾的时候。“香港当代艺术生态系列论坛”希望能够邀请到对香港当代艺术生态有着深入了解和实践经验的同道一起展开讨论,以此作为之后长期关注的开始。
裴刚:雅昌艺术网主编朱青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
惠雅婕: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编务总监
今天听完王纯杰和马玉江两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这两代人对比非常明显。我注意到王纯杰老师1983年就从上海到了香港,而马玉江是2014年才从北京到了香港,大概相差30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差,所以他们对于香港的观察、分享的观点和表达的思路区别都很大。两个人都是艺术家,王老师是特别多元的身份的复合体,既从事创作,又从事艺术的策划与行政工作。王老师对从1983年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跨度中,香港文化的情境、社会的制度、艺术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的概述,我觉得跟我的观察是接近的。对于我这代广东人来说,香港是个超级的商业都会和流行文化中心,像麦当劳、流行歌、香港电影,我们从小看翡翠台的动画片和新闻、港剧等,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香港像一个能量中心,所体现的主流文化不是当代艺术层面的先锋文化,而是商业的、消费主义系统里的文化。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香港文化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
昨天冯原老师从大历史和谱系的概念,对香港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和主体性问题做了勾勒。从我的观察来讲,我觉得香港一直在整体的中国现代性的框架里。香港的现代化出场是在19世纪中后期,但真正发挥影响并反馈到中国艺术与文化层面,则要到20世纪的下半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通过香港重新接受现代性的洗礼,跟我们在20世纪初所接受的现代化的思想路径又再接上轨,这可能带来了我们今天在中国内地能够体会与共情的一个艺术语境。而我所在的深圳更是在最近40年里被塑造成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典范,主要是因为有香港的带动作用。深圳的整个生产、消费、审美和治理技术都是从香港移植的。而且,深圳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农业县发展成超级都会,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被定义为核心引擎和创意文化中心,其实是因为接受了经香港引介的现代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段里,把香港当作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世界的渡口。我们通过香港的文化能找到一个窗口,既接续古典意义的文化中国,又为珠三角的当代艺术提供了动力。比如说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启动的阶段,从香港流入广州的信息多少触发了像南方艺术家沙龙、大尾象这些艺术群体的主体自觉。而且,广州媒体文化的土壤也受到香港充分市场化的媒体氛围的催发。
不少从北方来广州、深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有香港的吸引力。就我的工作经验而言,我2008年在广州读研究生时来深圳做实习生,首次去香港出差是替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去做执行工作,深圳会把包括香港当代水墨、日本当代水墨、韩国当代水墨、新加坡水墨等等,包括王纯杰老师讲的从传统水墨转型实验到现在跨媒体的、带有东方美学的实验艺术体系,放到泛水墨美学的广角下来透视。所以在珠三角地区,可能有种跟传统的中原中心不一样的边缘视域,我觉得这是地缘属性给这样一个区域带来的一种意识/结构松动。我们知道人类学家斯科特写过一本书叫《逃避统治的艺术》,虽然主体研究的是在东南亚的左米亚高地上生活的族群文化,但是事实上与朝向水域、朝向海洋的珠三角所带有的这种相对松动的文化土壤是相关的。作为一块相对边缘的、跟西方通商的前沿区域,香港在碰撞中比较早就激发了本土意识,比如我们看到香港的九龙皇帝的书写行动,还有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资深研究员翁子健从2009年开始跟广州艺术家合作发起的观察社,就是一个艺术替代空间的实践,通过对最新的艺术实验的支持去联动地域,推动新艺术的发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民间自发行为。香港曾经并不具备特别明确的文化主体性,但是重商主义带来了商业的成功和资本的积累。当资本需要进行价值转化时,汉雅轩、拥有三四十年历史的老牌画廊、艺术家自组织空间以及亚洲艺术文献库等拥有相对民间的造血机制。比如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它针对亚洲范围内的当代艺术文献的收集整理,可能也是因为香港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认同。香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段里,似乎并没有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当代艺术系统里所认知的特别强大的机构生产。正如王纯杰老师所讲的,权力的忽视和人才结构的缺失造就了没有系统的文化自觉和输出。如果单纯从消费或流行文化的层面来看,香港的影响力极大,但是在当代艺术的层面,我们似乎找不到香港在过去50年里朝外的自我积累、自我言说。不过,在整个当代艺术的体系建构和基础设施的重新定位上,香港官方的文化系统可能正重新给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坐标系,也许可以把M+的出现当作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艺术和文化事件。
[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对比王纯杰和马玉江两位艺术家所分享的内容,我们看到由于代际差别,艺术家的表现语言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艺术本身自带传承与想象的意义。可能王老师更多是在一个艺术系统内探索,是嫁接一个地方的文脉,是文化艺术意义上的考古。而马玉江所做的,我觉得源于一种当下的考现学,好比阿甘本所讲的赤裸生命,直指生命政治的底层而把现实的沉重和冷酷通过艺术的语言转化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批判现实层面上运用艺术的一次救赎行动,可能也是在最近十几年里香港社会语境变化和身份焦虑的情境中艺术家的一种选择与反馈。
我2003年到广州念书,之后跟香港艺术圈的接触更多是始于艺发局有了艺术推广计划,有了白双全,有了AAA和广州美院油画系的第五工作室,跟香港建立了学术与地域的联动。我逐步生成这么一个笼统的印象: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里,相当多的香港艺术家或艺术社团的表达方式还是日常美学的经验转译,这个部分的构成可能占比会大一点。比如我记得大概在七八年前,香港艺术家林东鹏临时包下了湾仔的一个酒店,然后在酒店的房间里,利用窗台、地板、床铺和浴室做了他的个展,把艺术的创作和美学的关注拉回到生活空间的维度,可能是受到香港的景观社会和消费文化驱使而做出的一种审美日常性的复归。
李老师讲得蛮好的。其实从2005年我结束了在艺术发展局的任期之后,就很长时间在珠海、在上海。但是,我的家一直在香港。在上海工作时,我每个月都回港,但香港的艺术活动我参加得就少了。你所说的艺术家从私密个人的生活空间去发掘,其实在90年代后期就有。2005年左右,一些团体就停止活动了,还有一些团体继续存在。原来在80年代和90年代,整个社会的心态都比较包容、多元。原来只是有些小圈子文化,后来因为出现了“身份”的焦虑,引发了一些社会思潮,出现了分化问题。
我一直特别重视香港的情况,这一点纯杰最知道的。我们重点关注香港,主要是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大陆遇到了当代艺术发展的困境。困难到什么程度?1998年王南溟做了一个大陆和香港的联合当代艺术展览“98中港装置艺术展”,这个展览在开幕前一个小时被封掉了,封闭的理由不是说这个展览方式和内容不能展,而是说这条街今日停电。之后展览开到哪里,哪里就“停电”。最后王南溟想了一个办法,把所有展品放在一辆大货车上,把大货车停在停车场,停了较长的时间,这个时间长度让人感觉此事已经不存在了。突然王南溟找到一个电影摄影棚,立即把卡车开过去,立即开幕,立即组织讨论会,等到再停电的时候,展览已经结束,开幕已经完成,讨论会已经做过。当时香港的合作者在开始遇到困难时就说“我们不做了,我们走了,我们不想跟你们这边的人发生矛盾”。当时是由我陪王南溟去谈判的,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香港的艺术家留下来跟我们完成这一次的当代艺术的抗争,但是他们不愿意,我们也没有办法。
后来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造成了第二个时间点。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性质有了根本变化,突然变成了当代艺术展,一直延续至今,俨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双年展之一。这个展览开幕以后,所有其他展馆和画廊的当代艺术展马上都可以公开展览,不再查封,而且这些展览都比上海双年展要激进得多。但不出所料,紧接着国内当代艺术就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反复。北京由美协开始筹备“北京双年展”,规定只许展出架上作品,也就是反装置、反录像、反观念艺术,就是公然地用保守主义的传统艺术观念和方法跟上海对抗。再看上海。上海虽然冲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是立即选择撤退坚守,所以2002年第四届的上海双年展主题是建筑,2004年第五届的主题是影像生存,到了2006年主题是超设计。虽然还是双年展,但是这三个题目已经无关痛痒,不再主张激烈的观念性。
此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以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下一步发展现场一定会是在珠三角,因为这里有香港。于是我就频繁来到广州和深圳,在广州见了很多人,动员他们做当代艺术。我们也到香港,记得住宿在油街的停尸房改造的工作室里,在阴冷的夜里,手抚停尸台,想着香港的伟大的可能性,充满期望。真的是这样,当时我们也不能睡觉,因为那个停尸台是水泥做的,虽然已经被不断冲洗过,但水泥缝里似乎还有尸体留下来的味道,使得我当时出现了幻觉,就不停地抚摸这个停尸床,才能使自己安定下来。那么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在这样的地方还在幻想?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开放制度和地理位置,有可能为中国的当代艺术留下一个继续发展的机会。当然,后来王璜生在广州创办了广州三年展,不久后黄专于2005年建立了OCAT,这个时候开始在珠三角看到的当代艺术的曙光至今明亮。而自从2000年我们意识到大陆会出现一个低潮和反复以来,就希望香港能够替代上海走向进一步的辉煌,把上海双年展第三届带来的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开放的口子迅速扩大。但是很可惜,这件事情没能够在香港实现。我们都作了努力了,王纯杰老师的努力更深更大。说实在线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香港。直到M+出现,我就发现,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预先假设不对,就是引领香港的是商业和产业而不是事业。乌里?希克这样的商人操作者是可以推进艺术的发展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没有义务和责任,而且他们根本上没有中国人具有的近代史屈辱。香港人应该有更深的体验,但是对于引领世界以复兴民族的雄心,香港人不知是不是没有做好准备。香港给我们的最终的教训就是,商业实际上是不能够作为事业来推动艺术的发展。如果艺术是一个产业,如果艺术的收藏和展览是一门生意,艺术最多也就是金融和娱乐的集市。所以香港给人的印象是,虽然把艺术做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毕竟是个商场。不过,我们纵使对在香港从事当代艺术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和警惕,但是随时等待着香港的升华。倒是最近几年我在反省,我觉得我们在大陆对外国人做的中国的当代艺术的推进重视不够。我后来还在西安的一次艺术史理论会议公开大会上做了检讨,特别是我们北大的档案好像不太重视外国人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的贡献,比如尤伦斯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乌里?希克的积极作用等。
有了M+以后,我从双重的角度来看待新的香港当代艺术基础:一方面这件事情是香港文化和艺术的一次崛起,是向世界再一次展现自身的位置和潜力,又使我们看到了一次曙光;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把乌里?希克的收藏作为主体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和进程”,容易造成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片面化印象,而不能自我整理和表述,就不能昭示未来的机遇和前程。
M+开了两个月了。开幕那天我去看了,参观的人很多,我较快地看了看。如果从香港文化需要的角度来看,M+的定位肯定存在问题的。香港将成立新的文化局,有必要重塑文化政策和重新审视香港艺术馆、博物馆包括M+的定位、发展方向和运作模式。如果以乌里?希克的藏品来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那偏错就很大了。希克在欧洲用他的藏品做了那个叫“麻将”的中国当代艺术巡展,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后殖民文化方面的批评。我在欧洲看过这个展,也曾在上海的一个艺术研讨会上谈过我对这个“麻将”展览的看法。
各位老师从各个角度讲述香港的当代艺术面貌,尤其是王老师,一开始就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形成丰富的艺术创作,以及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并回顾了跌宕变化的香港当代艺术发展历程。
马玉江老师又从个人化的艺术实践,把香港今天的当代艺术生动鲜活地拉近到此刻。而这部分的信息,我们在做内容的过程中较少能够涉及。今天朱老师推动的这个论坛,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和视角。我也参加过几次在香港的艺博会,当然艺博会更趋向商业化,不是从学术或者美术馆的角度,展出作品也更多是架上的部分和经典艺术部分。香港本土画廊代理香港艺术家的作品,也有香港画廊代理内地艺术家和国外艺术家的作品,也都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的。马老师对个人的艺术实践的介绍,从感触最为真切的现实人物、事件的田野考察的方式介入,形成他的作品表达和语言方式,用现成品的方式表达,形成非常理性的叙事线索,而且视觉的表达也非常有力量,对于我了解香港当代艺术的在地性经验是一个补充,尤其是从香港当代艺术多维度的丰富性层面来说,带来的感触是非常真切的。
朱老师谈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大的变化和转向。在北京周边生活着很多当代艺术家和工作室,形成了当代艺术生产和展出的便利条件。近些年上海的艺博会和画廊市场的活跃度显而易见,更具有商业环境的优势。朱老师提到了这个转向,确实需要深入思考,更多地讨论。香港M+开幕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跟进报道,还没有展开常态的深入内容合作。我们更希望了解香港本土当代艺术在地性的创作状态、正在发生的艺术创作,参与到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机构正在关注和发生的艺术项目中去。
那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应该多找一些在香港的人参加论坛和对话。其实我们今天谈话,都是在大陆与大陆相关的人谈香港,还是隔岸观火的感觉,感情和反应方式多多少少有点隔阂。也许我出面,大家一看就觉得是自以为是、自我中心主义,就厌烦得很;换成另外的一个角色,也许雅昌出面好一点,在这个平台上谁都可以说话。我们就继续再深入一点了解香港,请大家帮帮忙,找到香港的当地人,跟我们说心里话,这个才有意思。我们希望他们发声,我们愿意记录他们的行为轨迹,观赏他们的业绩。
好的,这个论坛也把各方面的资源拉到我们眼前了,那我们就可以去进一步拓展,有更多的选题介入,可以请更多的艺术家和机构,以不同的视角来讨论。
各位老师陆续聊了之后,解开了我的一些疑问,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感受。我也希望邀请更多香港本地的艺术家来。其实我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也访谈了一些艺术家,当我以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的身份去发出邀请的时候,那边是欣然接受的。可是前段时间和雅婕组织论坛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有在发邮件,要么就不回我,要么就委婉地拒绝,让我一度产生了怀疑,觉得是不是我措辞不当,还是说人格魅力不够。
后来,我想可能就是有一种所谓“无形的边界感”存在,这个问题也同样产生于我博士论文里面的发现。例如今天各位嘉宾老师都是不同时期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我观察到在九七回归前,除了王老师,还有潘星磊等其他一些内地过去的艺术家到了香港做的作品,也延续了跟内地时期有所连接的实践方式。我发现从内地到香港的话,很快就会融入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城市环境里面去做作品,作品加入了一种香港的在地性。但是,从香港进入到内地去做作品的艺术家多多少少是会存在一些所谓的边界感的,夹杂着某种恐惧。我不知道这个形容词对不对。
“边位?—— 香港艺术家十二位”群展,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费家村1号,2003年12月27日-2004年1月15日
比如说我注意到2003年有一个小展览,叫做“边位?——香港艺术家十二位”,是香港Para/Site空间和北京的张朝辉策划的,在北京费家村酱艺术空间做的。这个展览也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支持。之后他们出了画册,也写了一些文章。不过这个展览到现在找到的资料非常少,我也是花了好久时间才找到当时的这本小画册。这里面就有非常珍贵的香港七零后、八零后的几个艺术家写下的只言片语,描述了他们第一次到达北京时带有非常兴奋的情绪,但是下机场之后,一行人挤在一个小面包车里面,一路经过了大裤衩大楼,慢慢地颠簸到城乡结合部的时候,他们心理上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而且还有一个女艺术家在博客中记录下开幕的时候,来看他们这个香港艺术家展览的观众寥寥无几,但同一天在另一个画廊开幕的是在内地当时非常火爆的某位艺术家,这导致两边捧场展览的观众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现场,有一个本地的策展人就向这位香港艺术家提出了建议,说建议他们到内地做展览,应该多做一些行为艺术,这样的话可以引起媒体的报道,然后可以吸引眼球,也可以让他们的作品在内地更好卖。这个艺术家也没有发表任何的看法,她只是忠实地记录下了这段话,所以这个展览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而且,正如这个展览的名字在粤语里面表示的是“我是谁?”、“你是谁?”,同时,“边”代表了“边缘”,一语双关地指出“是谁?”或“边缘的位置”,所以这个展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有必要把它重新考古挖掘出来,进行一次研究对比。当然这个展览里面的艺术家现在去了哪里,活跃度如何,他们是否再次参与到了内地的一些交流里面,这种跨地的流动为什么而流动,流动之后带给他们的心理变化是怎么样的,我认为也是蛮有趣的。今天我们这个第二期的论坛的人员构成,几乎都是内地的或者有内地生活经验的。昨天第一期的论坛,我们也有珠三角的嘉宾,那么珠三角在香港、北京、上海中间又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想还是得回到艺术实践上来说。按照我的一点实践上的经验或者是一点观察来看,我认为北京是一种宏观大气的感觉,上海非常精致商业,珠三角这边是一种生猛,它会出现像大尾象、郑国谷一类的生猛,也会出现不像学院派的学院艺术家。那到香港,反而是回归到一种细腻,这种细腻可能是跟它的日常生活局限有关。像马玉江老师到了香港之后,我注意到您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像情书、像一些跟您母亲的这样的一种对话,那虽然是很私人的,但是我认为正是这种细腻的情感在香港才得以继续升华出来。也就是说,反而是在香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能够凸显出您骨子里这种细腻情感的珍贵性。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在2020年,朱青生老师和我们在坪山美术馆实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9”,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档案与中国当代艺术”的闭幕论坛,朱老师和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的翁子健都是演讲嘉宾。就今天论坛的题目,我想起翁子健2015年在Para Site跟当时的Para Site艺术总监康喆明联合策划过一个展览,叫“土尾的世界——抵抗的转喻和中家想象”。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出色的展览,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接续了香港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中国遭遇现代性乃至当下的历程,以视觉和思想史的关系来勾勒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精神与主体性观照。
有一点我觉得朱老师讲得蛮对的,就是在一个关于香港艺术生态的论题里,对于在香港出生的艺术家,他们的认同感和情感转化,我们是否可以直接地碰触得到,这是个问题。但是像马玉江和王纯杰老师,他们在香港可能有接近10年甚至40年的生活经验,不同代际在香港的代入程度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所牵带出来的跟本土香港的认同和想象之间可能存在磨合与拉锯的关系,也是今天需要被关注、被重视的问题。这个系列的讨论如果要往前深入的话,这是值得挖掘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现在身处深圳,我觉得从城市的艺术结构来讲,深圳跟香港的问题具有蛮大的同构性,因为香港没有一个独立或者相对完备的艺术学院建制,深圳也是一样。我们知道香港在最近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很多艺术家都是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或者是城市大学出来的,他们接受的教育在综合性研究、在人文通识教育上的重视程度,具备卓越的现代大学的高度,实际上是我们所欠缺的。
我补充一点。刚才朱老师讲对香港的文化艺术研究是一个对香港历史的认知方面,通过文化也能够了解香港的社会发展。去年底有一个年轻人找我,说很想采访我。我说为什么,我在香港目前也少有活动了,我的工作主要在内地。他告诉我,他自己正在做香港民间艺术团体的历史档案记录,他发现90年代的最活跃的青年艺术团体以及那些有影响的、当时媒体报道也很多的艺术活动和艺术现象,现在没人提起,这些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他说现在有重要艺术机构也有人去回顾90年代香港艺术的历史,都避开这些艺术活动和艺术团体。他觉得应该把这个历史重新复原,有些东西不能忘记。所以他特地找我,因为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最活跃的的事情我很多都有参与的,让我把那些90年代历史的艺术的资料提供给他,他会放在网页上。我想那些只有在当时香港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生的有影响力的艺术现象和活动不应该被“忘记”或被“回避”。这些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发生的有意思的艺术现象,以后是不能重复的。历史需要记忆,文化需要积淀,这样才能有益于香港文化艺术。以往也没有任何香港的艺术机构主动问我要过相关资料。那么我就开始整理身边的资料,提供给这位年轻人。也就是说,我在这个论坛开始之前就已经在整理相关的香港艺术资料了。
好,我发给你们我所保存的一些香港艺术的资料。我是以个人的经验经历的视角,在那个时代我能知道的,我都会放上去,不会回避的。历史中发生的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大家都可以表达不同的看法,但历史上曾发生的事实就是事实,这是一个对历史的态度。
那么第二个就是身份的问题。香港居民成分是很复杂的,港人的身份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的。香港至今都是人口进出移动性很大的城市,一个重要特征是有漂浮感。绝大多数各地移居到香港的居民认同这里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环境,并认同这里的文化,把家安置在这里,生儿育女,投入本地社会。不能把移居的社会群体简单地都划为“过客”,这不是社会的线年代以来发展出来的香港的文化与艺术,对香港本地文化意识的产生起了很大作用。香港文化艺术的本地化发展,是多元的社群在多元文化的交汇同创造的。如果强调只有本地出生的人才是香港本地文化艺术的创造者,这不是社会事实。这种以社群分割的艺术史的叙事,抹平多重社群的文化努力,会失去香港的多元文化创造力的优势,香港艺术就会萎缩。这种态度既不符合当代国际社会的价值理念,也会产生社群之间的裂痕。我们能从这十多年香港文化艺术创作缺乏动力的状况,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所以香港的艺术家从哪里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他是不是融合在这个社会里,参与投入在社会里,自己尽力去推动一些文化的事情,关键在这里。
相关文章
- 透水砖唐山透水砖厂唐山透水砖
- 10月1日至3日支付3倍工资 其余4天支付2倍工资
- 遂宁膜结构景观棚订制设计
- 世界人居网·精品丨广东佛山:西江沿岸区域城市设计及景观规划
- 斩获国际大奖它凭什么?
- 喜讯 JZFZ成都景观公司斩获第十一届“园冶杯国际竞赛”三项大奖
- 涨知识盘点那些奇妙的自然景观
- 江苏徐州:从绿水青山到园博盛会在这里看见“美丽中国”
- 魅力十足的雄伟山岳景观与传统街景!中部地区简介
- 杂色鹅卵石建筑景观材料 鹅卵石景观室内装饰石
- 院士领衔参与!广州举办全国首个变电站景观及功能设计国际竞赛
- 园林景观设计的九种方法 实战干货分享
- 【新作】这才是顶级售楼中心设计该有的气质!
- 潍坊恒信·春光里打造全龄社交景观园林致敬懂生活的你
- 植物风水学知识园林景观人必知!
- 四川“逆袭”的“土味”景区更名后走红被誉为“成都绿肺”
- 喜讯!鹤城欢乐世界成功晋升国家AAAA级景区
- 四川建园建材公司:这个“园林式砖厂”不简单
- 再迎新利好中建智地助推京西人居迭新
- 关于2022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瑞彩园林景观公司第三批苗木采购招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