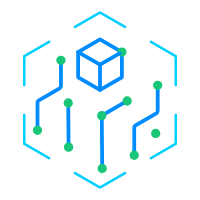重返废墟:当代国产电影中“废墟”景观的生产与再现
重返废墟:当代国产电影中“废墟”景观的生产与再现
重返废墟:当代国产电影中“废墟”景观的生产与再现,景观插地灯,双轮景观塔,景观壁炉弗里斯比在《现代性的碎片》一书中这样说道:“社会理论家需要处理的独特问题, 是寻找那飞逝和过渡物之所在, 并捕获它。这不仅是齐美尔面临的方法论问题, 而且也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面临的问题。”这句话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学家及各类文化研究者的使命,找寻到历史变迁的边界与裂隙是认识当下社会来历、社会性质与社会结构的关键任务,自然这是一个极其繁重与庞杂的集体工作,这也使现代性问题成为当代最被热议但仍旧悬而未决的宏大命题之一。
本雅明和波德维尔在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上曾返回历史现象中,观察某种“破碎性”所隐匿的现代寓言。在《德意志悲苦的起源》一书中,本雅明提出了著名的寓言概念,寓言“是由一系列未能捕捉到意义的瞬间时刻组成的一个断续结构”,该书“通过对巴罗克悲苦剧中废墟崇拜的分析,本雅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废墟与寓言二者所存在的同构性:‘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1]本雅明通过废墟美学理论,深化阐释了其审美救赎的思想,“废墟”也在本雅明的现代性相关论述中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关键词。
而对于“废墟”美学的创造与认知,在浪漫主义盛行后众多美学家在方法与概念上也不断将其壮大,在电影方面,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将“废墟”景观以写实风格再现于观众眼前,那是些观众所熟悉的景象,二战后的断壁残垣、古老的遗址与城市的创伤,他们不再是银幕上一闪而过的单薄的视觉图形,而是同情感伴随的具有发散性指意的记忆倒影,““废墟”为影像提供了某种“裂口”(déchirure),借此能“撕开”影片中的虚构世界,揭示出复杂的时间性、隐藏的涌动记忆以及内在征候。”[2]
在文化思潮与电影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对“废墟”景观形成了本土关注,较为明显的是第六代导演群体,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后的土木兴工里,在混凝土代替土瓦片的过程中,这些人拿起摄影机纪录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轰然倒塌的工业与城建废墟。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废墟—现代城镇如何扭结成一个包含着异质性与破碎性的错乱时空,贾樟柯借助两段寻亲故事线串接起了奉节县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图景。在时间顺序上,镜头带领观众由长江出发,从自然景观过渡到不可见的历史废墟,当韩三明来到标记的寻亲地址时摩的小哥告诉他这里早已被江水所淹没,此时影片顺着韩三明的目光遥望着青灰色江水,历史遗迹在这里已不复存在,又或者说它仍旧存在只不过被泯灭在文明改造的潮水之中。
从这里继续出发,影片将故事铺展在底层人民进行劳动的可见的废墟空间中,可以说电影向观众呈现了一个活着的废墟,镜头略过的那些正在叮叮作响的劳动景象,以及叙事中不断提及的水位期限都在提醒着人们废墟正在不断的生成与消失,而另一端已被改造完成的城镇也表明,当下时代正是建立于一片废墟之上,人类在历史变迁中以文明之义剔除掉依赖自然进行栖居的土窝树巢,其中牺牲的不仅仅是坍塌的物质空间,还有底层群体那被动、无奈却又坚持驻守的精神世界。
废墟是第六代导演群体用以表现社会发展的重要景观,在城市空间内,工业废墟曾一度沦为“游荡者”的敌托邦,那些闯入城市的浪子面对城市空间以及由城市文明带来的现代秩序、混杂的生活内容内心回荡起危机的响音,于是“逃跑”成为了他们避难的选择之一。在《苏州河》中,马达最初以漫游者身份观察着苏州河并与之保持距离,而当牡丹坠河身亡后,他的身份开始向着“解谜人”进行转变。在上海,他所要寻觅的不仅是与牡丹丢失的情感记忆,还有他作为一名城市“他者”对现代精神逻辑的思考与解答,电影利用物质的城市废墟景观映照出该时代背景下的精神寓言。
“城市废墟景观作为一种具象空间,它不仅能够跳脱时间之维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寓言化在同一个物质空间里,同时它还承载着集体对于某段过往经历的情绪记忆,这是城市废墟能够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而非无意义废弃物的重要原因。”[3]电影《春江水暖》中的废墟景观便形成了诸如此般记忆、当下与未来的共时性空间。在老三去索要欠款的段落里,镜头穿越迷雾将观众带入一片时间错杂的生活废墟中,破败的楼宇间处处横挂着宣传条幅,暗示出这是一个城市有机更新下的旧细胞。
当人物进入这样的地界,镜头选择在不同的空间位置进行游移,杂乱的道路像是不同维度下的走廊,镜头利用景观特征创制出了多重嵌套的异质时空,在这里工人读着寄于往日的信笺,老三的记忆坠落在损坏的电视机中,梦境与现实交缠在昼夜,废墟变成了一个透明却又叠态的诗意迷宫。
“城市废墟看似是一处处似乎已经被城市遗忘乃至废弃的建筑,但实际上城市废墟却是以一种碎片化的书写方式,将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呈现给观者,而摄影机是这些破碎信息的最佳聆听者。”[4]《钢的琴》将大烟囱的衰亡祭奠于下岗工人的手中烟,与之一起凋零的是曾经辉煌的东北工业文明,然而旧的遗址凭借宝贵的时代精神仍然能够造出新时代的钢琴,并在时代交替的分离之痛下敲出刚性且嘹亮的重音。蔡明亮的《郊游》则将废墟视为底层人民在当代城市焦虑中的一片诗意暗室,未名的野火烧空了关于此地拥杂的空间记忆,当小康久久伫于灰烬所作的壁画前时,废墟给予了他逃脱城市威逼进入精神避风港的契机,长镜头屏息注视其泪流满面,将人物含混的情感与记忆书写进空荡的废墟景观。
废墟是建筑的遗骸,也是历史即将松开的手。重返废墟,是携着当下经验寻找来时的路,同时,也是通往未来之途时留下未亡的骨。电影中的废墟景观表现出的异质性、破碎性与暂留性使其可以跨越维度呈现出个体记忆与集体情感的联结,此外它也诉说历史、审视当下成为探讨社会症候的空间标本。所以说,在废墟之上,我们得以仰望今日的星空,而在废墟之下,我们得以开垦无垠的历史。
[1] 《春江水暖》:废墟寓言的在地性表达,陈亮、李攀,电影文学,2021.06
[2] “废墟”与“影像”的“相遇”——“二战”后欧洲电影中破败景象的思考,李奇,当代电影,2022(02)
[3] 历史寓言、空间修辞与情绪记忆: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城市废墟,郭钟安,电影文学,2021(24)
[4] 历史寓言、空间修辞与情绪记忆: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城市废墟,郭钟安,电影文学,2021(24)
相关文章
- 四川又发现一处“怪石滩” 专家:河水上万年冲击河床侵蚀形成
- 绿满滨湖 大美横林——一起来感受风光旖旎的横林之美
- 乡住免费图纸 土建造价参考30万面宽146m×进深89m 一层现代风格乡村别墅
- 甘州区西街街道北关社区:景观小品扮靓家园 文明之风吹进心田
- 沂水:丹心映照晚霞红--社会福利中心刘燕
- 【我的共富故事】小苔藓大产业 温州文成乡村“微缩景观”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 美丽湿地|十大魅力沼泽湿地
- 2022年南宁花花大世界景区国庆收费吗
- 迎接国庆和二十大“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将亮相广场
- 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鑫荣游览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涉嫌非吸案最新通告来啦参与人速去报案登记…
- 济南绿城|匠心本源品质为先
- 关东车村:山水田园农家“乐”
- 赤峰交通:公路绿化 风光无限
- 当代景观规划的上海景观设计培训
- 观音山公园108万征下联上联:观音山上观山水绝对下联或出炉
- 奔赴“共富”路 浙江处处好风景
- 成都东部新区航线区域大地景观规划暨实施方案项目公开招标中标公告
- 重庆“飞天之吻”景观火了!网友评价褒贬不一直呼:看不下去了
- 2022公示洛阳全盛花园小区景观绿化项目招标公告
- 《怒海沉尸》有最帅的瑞普利和最黑暗的故事